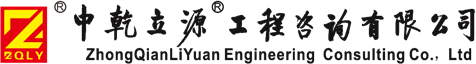毛澤東在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(wù)》中,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和清醒的階級分析,回答了“誰來領(lǐng)導(dǎo)中國革命”這一根本問題。這篇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的綱領(lǐng)性文獻,不僅為抗日戰(zhàn)爭指明了方向,更以其超越時空的理論價值,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觀察歷史、把握現(xiàn)實的思想坐標系。
一、歷史選擇:誰主沉浮?
1937年的中國,山河破碎,內(nèi)憂外患。國民黨政府一面消極抗日,一面圍剿紅軍;地方軍閥各懷異心,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。面對“中國向何處去”的叩問,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解剖刀,剖開了中國革命的本質(zhì)矛盾:資產(chǎn)階級的軟弱性注定其無法領(lǐng)導(dǎo)革命走向徹底,唯有無產(chǎn)階級才能肩負起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。
這一論斷背后,是對中國社會結(jié)構(gòu)的深刻洞察。彼時的資產(chǎn)階級依附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,既渴望打破壓迫,又恐懼工農(nóng)覺醒動搖其根基。這種“先天軟骨病”在1927年大革命中暴露無遺:當工農(nóng)運動觸及既得利益時,蔣介石集團毫不猶豫地舉起了屠刀。而無產(chǎn)階級“除了鎖鏈一無所有”的階級屬性,決定了它天然具有徹底的革命性。正如毛澤東所強調(diào)的,“使資產(chǎn)階級跟隨無產(chǎn)階級”還是相反,這是決定革命成敗的“關(guān)鍵之關(guān)鍵”。這種清醒的階級意識,在今天的國際變局中依然振聾發(fā)聵:當資本邏輯試圖主導(dǎo)人類命運時,誰能為大多數(shù)人的利益發(fā)聲?
二、領(lǐng)導(dǎo)權(quán)的辯證法:原則與智慧的平衡
文中關(guān)于“如何實現(xiàn)領(lǐng)導(dǎo)權(quán)”的論述,閃耀著唯物辯證法的光輝。毛澤東提出“四個條件”:政治綱領(lǐng)、先鋒作用、同盟策略、黨的建設(shè),構(gòu)成了多維立體的領(lǐng)導(dǎo)權(quán)實現(xiàn)機制。其中,“停止內(nèi)戰(zhàn)”“實現(xiàn)抗戰(zhàn)”等口號看似簡單,實則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轉(zhuǎn)化為群眾語言的典范——真理只有被人民掌握,才能成為改變世界的物質(zhì)力量。
更令人嘆服的是對“同盟者”關(guān)系的把握。既反對“左”傾關(guān)門主義“唯我獨革”的傲慢,又警惕右傾尾巴主義“降格以求”的妥協(xié),這種“既聯(lián)合又斗爭”的策略,在西安事變的處理中得到了完美詮釋:既推動蔣介石抗日,又堅持獨立自主。這種政治智慧,在當今國際交往中依然具有啟示意義:面對復(fù)雜博弈,如何在堅守底線與靈活應(yīng)對間找到平衡?
三、未完成的命題:民主共和國的雙重鏡像
關(guān)于“民主共和國前途”的分析,展現(xiàn)了革命者的遠見卓識。毛澤東指出,這個“各革命階級聯(lián)盟”的國家,既可能滑向資本主義,也可能轉(zhuǎn)向社會主義,而“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應(yīng)該力爭后一個前途”。這一判斷打破了機械決定論的歷史觀,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納入歷史進程。
這種對歷史可能性的開放性認知,恰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始終保持戰(zhàn)略主動的密碼。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,從計劃經(jīng)濟到市場經(jīng)濟,黨始終在“歷史條件”與“政治自覺”的張力中探索前行。今天,當某些西方學者鼓吹“歷史終結(jié)論”時,中國道路的實踐恰恰證明了:歷史從不預(yù)設(shè)終點,人類的創(chuàng)造性實踐永遠在開辟新的可能。
四、永恒的警醒:與錯誤傾向斗爭
文中對“關(guān)門主義”和“尾巴主義”的批判,至今讀來仍如黃鐘大呂。前者以“純粹革命”自居,實則孤立自己;后者以“現(xiàn)實理性”為名,實則放棄原則。這兩種傾向在新時代改頭換面,表現(xiàn)為教條主義的“本本崇拜”和功利主義的“精致利己”。
毛澤東給出的藥方——“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”,絕非簡單的口號。真正的理論武裝,是掌握“活的靈魂”,是像文中那樣將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(jié)合的能力。當某些人把“中國化”誤解為對經(jīng)典的背離時,這篇文獻恰恰證明:只有扎根中國大地,馬克思主義才能煥發(fā)永恒的生命力。
結(jié)語:照亮來路的火炬
重讀這篇文獻,最深的感觸是:真理從不因歲月蒙塵。在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的今天,文中的核心命題——堅持黨的領(lǐng)導(dǎo)、依靠人民群眾、把握歷史主動——依然是指引民族復(fù)興的北斗。當某些人熱衷于解構(gòu)歷史、質(zhì)疑初心時,這篇寫于窯洞油燈下的文獻,以其穿越時空的思想鋒芒告訴我們:唯有堅守“為絕大多數(shù)人奮斗”的初心,才能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把穩(wěn)航向。
站在兩個百年的交匯點上,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“清醒的歷史自覺”。因為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(fù)興,從來不是浪漫主義的田園詩,而是需要以科學理論為羅盤、以人民立場為根基、以斗爭精神為風帆的新的偉大遠征。而這,正是這篇文獻留給后人最寶貴的遺產(chǎn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