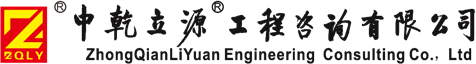子張篇2
子夏曰:“仕而優則學,學而優則仕。”
【評析】
子夏的這段話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針和辦學目的。做官之余,還有精力和時間,那他就可以去學習禮樂等治國安邦的知識;學習之余,還有精力和時間,他就可以去做官從政。同時,本章又一次談到“學”與“仕”的關系問題。
子游曰:“喪致乎哀而止。”
子游曰:“吾友張也為難能也,然而未仁。”
曾子曰:“堂堂乎張也,難與并為仁矣。”
曾子曰:“吾聞諸夫子,人未有自致者也,必也親喪乎!”
曾子曰:“吾聞諸夫子,孟莊子之孝也,其他可能也;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,是難能也。”
孟氏使陽膚為士師,問于曾子。曾子曰:“上失其道,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,則哀矜而勿喜!”
子貢曰:“紂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,天下之惡皆歸焉。”
子貢曰:“君子之過也,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,人皆見之;更也,人皆仰之。”
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:“仲尼焉學?”子貢曰:“文武之道未墜于地,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,不賢者識其小者,莫不有文武之道焉,夫子焉不學?而亦何常師之有?”
【評析】
這一章又講到孔子之學何處而來的問題。子貢說,孔子承襲了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,并沒有固定的老師給他傳授。這實際是說,孔子肩負著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,并把它發揚光大的責任,這不需要什么人講授給孔子。表明了孔子“不恥下問”、“學無常師”的學習過程。
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曰:“子貢賢于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貢,子貢曰:“譬之宮墻,賜之墻也及肩,窺見室家之好;夫子之墻數仞,不得其門而入,不見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,夫子之云不亦宜乎!”
叔孫武叔毀仲尼,子貢曰:“無以為也,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,丘陵也,猶可逾也;仲尼,日月也,無得而逾焉。人雖欲自絕,其何傷于日月乎?多見其不知量也。”
陳子禽謂子貢曰:“子為恭也,仲尼豈賢于子乎?”子貢曰:“君子一言以為知,一言以為不知,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,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,所謂立之斯立,道之斯行,綏之斯來,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,其死也哀,如之何其可及也?”
【評析】
以上這幾章,都是子貢回答別人貶低孔子而抬高子貢的問話。子貢對孔子十分敬重,認為他高不可及。所以他不能容忍別人對孔子的毀謗。
譯文
子夏說:“做官之后還有余力的就可以去學習,學習學好了還有余力,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。”
子游說:“居喪,充分體現出悲哀之情就可以了。”
子游說:“我的朋友子張可以說是難得的了,然而還沒有做到仁。”
曾子說:“子張外表堂堂,難于和他一起做到仁的。”
曾子說:“我聽老師曾經說過:人不可能自主地充分發揮感情, 如果有,一定是在父母死亡的時候。”
曾子說:“我聽老師說過,孟莊子的孝,其他人也可以做到,但他不更換父親的舊臣及其政治措施,這是別人難以做到的。”
孟氏任命陽膚做典獄官,陽膚向曾子請教。曾子說:“在上位的人喪失了正道,民心離散已經很久了。如果審案時審出真情,就應該悲哀憐憫,而不要沾沾自喜!”
子貢說:“紂王的壞,不像傳說的那樣厲害。因此,君子非常憎惡居于下流,一旦居于下流,天下的一切壞事壞名都會歸到他的頭上來。”
子貢說:“君子的過錯好像日食月食一樣。有過錯時,人們都看得見;改正過錯的時候,人們都仰望著他。”
衛國的公孫朝問子貢說:“仲尼的學問是從哪里學來的?”子貢說:“周文王和武王的道,并沒有失傳,還留在人間。賢能的人可以了解它的根本,不賢的人只記住了細枝末節,周文王和周武王之道是無處不在的。我們老師何處不學,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師傳播呢?”
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對大夫們說:“子貢比仲尼更有才能。”子服景伯把這一番話告訴了子貢。子貢說:“就用圍墻作比喻吧,我家圍墻只有齊肩高,從墻外可以看到里面房屋的美好。我老師的圍墻有幾仞高,找不到大門走進去,就看不見里面宗廟的雄美、房屋的富麗。能夠找到門進去的人并不多。叔孫武叔那么講,不也是很自然嗎?”
叔孫武叔誹謗仲尼。子貢說:“這樣做是沒有用的!仲尼是毀謗不了的。別人的賢德好比丘陵,還可超越過去,仲尼的賢德好比太陽和月亮,是無法超越的。雖然有人要自絕于日月,對日月又有什么損害呢?只是表明他不自量力而已。”
陳子禽對子貢說:“你太謙恭了,仲尼豈能比你更有才能?”子貢說:“君子的一句話就可以表現他的智識,一句話也可以表現他的不智,所以說話不可以不慎重。夫子的高不可及,正像天是不能夠順著梯子爬上去一樣。假如老師得到國家去治理的話,說要立于禮,百姓就立于禮;引導百姓,百姓就跟著實行;安撫百姓,百姓就會來歸服;動員百姓,百姓就會協力同心。他活著時榮耀,死了令人哀痛,別人怎么可能趕得上他呢?”